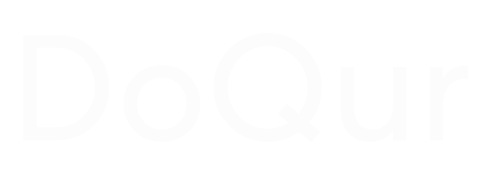也說《爱情神话》:現實生活中微弱唯美已屬難得,買菜小市民亦有真實的力量
由徐崢、女星、倪虹潔和南宋執導的電影《爱情神话》上週公映,影片展現出了一個定居在北京市中心的中年男人的感情糾葛。
現階段發生的評論家很多都是圍繞電影的外部展開,諸如對北京性、女權主義和階級意識方面的深入分析,卻缺乏對電影內部諸如敘事內部結構、詩意和藝術風格的評價,也缺乏與北京真實生活風貌的連結,使得許多抨擊聲音文檔分析嚴重不足且結論相對統一。這類評論家常常最終返回對北京懸浮貨品生活、虛假歲月靜好的批判中來,卻原地踏步無助於加深我們對電影的深探,本文企圖從內部解讀文檔,圍繞電影的現實生活美感唯美、閒話敘事和與北京實際生活的關係展開。
題為“希臘神話”,實際就像主人公老白所言,老烏的人生充滿著了希臘神話,他他們的人生充滿著了段子,陳女士笑說,這句段子蠻好笑的。希臘神話與段子原本不容並存,老烏講訴他們與索非亞·羅蘭的唯美一夜,點題“真愛希臘神話”,隨即馬上用笑談“我編的”開頭。段子一發生,希臘神話馬上土崩瓦解,老烏被人罵“十四伐”。
閒話的另一個功用是側寫下人物的真正形像。像是老烏與老白爭吵,老烏怒氣衝衝評點老白身旁的三個男人——一個是老菜皮,空虛,交往過後像糊豬油一樣甩不開;一個吃過中餐、開過眼界,交往之後不知要賠多少錢。陳女士的兒子瑪雅只不過也跟老白無意透漏過,爸爸儘管有QQ上的追求者,但事實上門付出的只有老白一個。三個男人認為都光彩奪目,攤到實際交往的層面,又都有無法克服的問題。正即使知道了這點,老白才深感無法接受。老烏與老白在男性賞鑑方面自然是相同的,但國際標準不能逐條公示,而是藉由閒話裡道出。陳女士在老白家門口扭斷的名牌衣服,也是兩條惹來無數閒話的線索。小鞋匠都窺見尺碼同前夫一樣,平底鞋所暗示的風尚和親密在每一人內心深處都很明晰,但又沒有人真正挑明。
這種具備反希臘神話機能的段子,假如被解讀為生活的麻藥,只能說明反對者對笑的理解僅僅逗留在逗笑上,不知中年人的段子有雙重涵義,如約翰·沃特在《不负责任的自我》中所言的,好的風趣有雙重性質:一重是寬容與規範世界相同的另類世界,另一重則是對我們正處於同一個世界的證實,傳遞的是共同的無力感。陳女士後來覺得“老白的人生充滿著了段子”好笑,也等於在感情上為老白放行。從片尾對於一場戲劇作出截然相同的反應,自己二人總算在“覺得好笑”上走到了一同,這為什麼並非對走過下坡路人生的最好安慰?
就像老白與老烏原本互為影子,說要談情說愛,電影的絕大部分章節都回蕩著段子。很多是更讓人啼笑皆非的、不合時宜的段子,比如說老白跟女兒男朋友不小心透漏前夫婚內不忠心,皮鞋匠的coffee time也屬於這一類。還有一類是有意識地與“真愛希臘神話”形成對照的真愛段子——如果說希臘神話是神聖嚴肅的,段子裡就帶有含混通融的情分,這好似代表著三種迥異的情感模式——孩童不再堅信希臘神話之後,反倒能即使段子氣味相投。
編輯 | 黃月
兩人在片場邊吃盒飯邊聊天,你一句我一句地促進感情漣漪,陳女士說,“得不到最好的,寧可換條路走。”老白問,“路好走嗎?”陳女士嘆道,“是走下坡路,有的好嗎?”老白忙接應,“下次約你去爬山。”在齊聚一堂的那晚,老白燒了一桌菜,四個男人品鑑出相同滋味:陳女士嗔怨,說好私房菜變為大鍋飯;前夫蓓蓓也不甘示弱,剩飯也有野貓搶;Gloria倒則表示,做野貓吃完了揩揩耳朵走了蠻好。
同樣是講訴北京感情故事情節,在許鞍華編劇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裡,斯琴高娃出演的姑媽在北京之所以顯得“任性”,不但是她中年以後還能和一個來歷不明的灑脫女子(張家輝飾)曖昧——當然也要承擔遭受情感騙子的危險——也在於她可以自由地上市場買他們討厭吃的小菜。返回西北之後,姑媽重新與當年的妻子和兒子續上前緣,她的境況的確變得更加牢靠了,也更“身只好”了,在菜市場裡,姑媽趴在地攤上吃饅頭就鹹菜,看上去與灰濛濛的環境完全相得益彰。
至於苔條黃瓜、蜻蜓酥、法棍或英式咖啡,都很難說是多么精巧中高檔的食材。對外貿易珠寶店時常是來路不明的“對外貿易原單”集聚地,用老闆娘如果說是“騙外國人的”。臨期肉類零售店更是物美價廉又有懷舊氣氛的地方,熟識臨期零售店的觀眾們會了解,這兒販售的糖果、啤酒和巧克力都遠高於大型超市平均價格,店裡客人分享著用啤酒洗臉或澆花的生活小妙招,也都是市民熟識的街頭笑談。那些物件更多承載的是現代人對同幾塊親切地界、同一種熟識食材的回憶,而絕非人云亦云的網紅營銷。
絕非所有物件都指向消費,絕非只有殘暴才代表現實生活
徐崢出演的主人公老白身分儘管分成多層——藝術家(非知名)、貝斯手、大廚、著名詩人——但都變得實用性大過唯美感。片頭,徐崢出演的老白與女星出演的陳女士趴在小劇場中,四位舞臺女演員低沉地吐露內心獨白,陳女士或因聯想到身世灑下幾行淚水,而老白只是打瞌睡,對故事情節全無心得。片尾也是如此,親密的夥伴們在老烏的告別式上一邊看費里尼的《爱情神话》一邊打哈欠,陳女士剛好拿起智能手機與在廚房裡準備小食的老白“暗通款曲”。就算是最“出格”的唯美夜裡,也未獲得被告的大肆宣揚——陳女士從那一夜中急忙逃脫,老白給精心準備的愛心煎蛋午餐當頭一叉;Gloria倒是含含糊糊表達依戀,實際卻將她與老白之間的關係越攪越渾,並沒有想讓唯美搬上大臺面的意思。
電影中的人物互為補充,線索明暗交替,共同大力推進故事情節經濟發展,頗很多“穿插藏閃”畫法的運用。至於四個主要男性配角,陳女士約看劇在前,Gloria學寫字在後,前夫蓓蓓的境遇透過小鞋匠之口透漏。在兩天夜晚,她們分頭大力推進的四條線索總算匯於一點,那場家庭聚會既充滿著了巧合、誤解和火藥味,又有如《红楼梦》怡紅院夜宴群芳般奼紫嫣紅,四位男性即使彼此間的存有而更被激發了表達本性的慾望。
更容易被我們忽視的,只不過是重重的生活詩意背後常人的生活形式:老白在結識陳女士和瑪雅之後,會去臨期零售店、咖啡廳買東西,他路經的鞋匠鋪旁邊就是小提琴專業培訓店;老白接瑪雅放學,領著她去咖啡廳寫作業;老烏為老白尋到的這些不靠譜的個展展館,更是一次北京公共空間巡展——從甜品鋪到美術館、咖啡店再到書店,人物在公共空間中穿行,他對一切都那么熟識,又心存歡喜;老白在敲陳女士門時聽見一陣陣提琴聲,尋鞋匠時又有小提琴聲伴奏。這也更讓人不由得想到,張愛玲寫他們在春夏前夕買菜路經門店時,聽見無線電娓娓唱著申曲。那時,她看見從菜市場回去的女傭、拎著鍋走過的小男孩,以及肉店裡的學徒和女顧客,他們拎著網袋,裡頭裝著瓶瓶罐罐,心生歡樂:
過著買菜洗衣服、一日三餐的生活的普通人,註定並非引領偉大革新的英雄人物,但常人的生活就是死水一潭、不值一提的嗎?就像張愛玲寫給的,在菜場買菜的、打著補丁的小市民也許才構成了中國前途。“超越的、革命的”與“和諧的、常人的”之間的關係或也能一辯,就像張愛玲曾說的那般——“鬥爭是一時的,是為的是實現常人的目標,平平穩穩過日子。”
電影中還有一名關鍵男性不容忽視,那就是老白的爸爸。她時常不聲不響送去飯菜並順走東西,用實際行動監察著女兒生活中的風吹草動。爸爸與前夫相繼發生,解釋了老白為什么處在一種懸而未決的中年生活當中,爸爸的造訪暗示了前夫的試探心態,而前夫與他見面又經常傳達爸爸的旨意——她們倆根本不須要同時發生,但又達成了聯手共進、“抵擋外敵”的同盟。處理現實生活中複雜關係的現代人也許正是如此,並不總會真正短兵相接,這一重關係的糾纏也是《爱情神话》富有寫實思想的彰顯。這對前婆媳傳話又互為補充地公佈出了老白曾經艱辛生活、現在白白討艱辛生活的真相,她們深信經濟發展事宜對外不容妥協,但巧妙的是,也不須要鬧到不容開交,只須要透個話風、試探深淺就可以。
假如純粹將該片解讀為高高在上的北京本地中高階層圖像奇觀,也許忽略了電影中力圖展現出的日常性。的確,主人公老白變得如此無所事事、有錢有閒,但他的閒情並並非故作優雅飄蕩於空中的,他去臨期零售店要問折扣貨品在哪裡,買名牌衣服也要估量他們是不是經濟發展整體實力。陳女士的境況更是不難理解,離婚後和爸爸擠在一同,電機採用都嚴禁自由,跟自己說要將小孩送去國外,叮囑小孩把他們少說幾歲;臥室狹窄擠迫,名牌衣服穿了好久,未來全無著落;對女人的考量裡無法沒有經濟發展不利因素,但要仰仗對方“施捨”給他們一家住宅時,又覺得虧欠太多須要斷舍離,這便是再常用不過的境況。Gloria是其中較為浮誇的人物,也只有她的故事情節(臺老婆在外國被殺害)聽起來那么難以置信,但是她織成出這種的老婆奇遇,也是為的是能有理由與老白交往下去。
“希臘神話”裡的閒話現代文學
儘管名為希臘神話,影片的重點並不在於最終希臘神話的點題。全劇並沒有營造“希臘神話”的氣氛,展現出的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此種感情在一日三餐、接送孩子、瑣碎閒話中週而復始,稍不留意就消磨殆盡。故事情節也因而缺乏話劇最高潮,稍顯唯美氣氛嚴重不足。但是,微弱唯美不便是普通人在生活中能找尋到的真實體會嗎?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補丁的彩雲的網友。……我真開心晒著木星去買來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我們可以說影片中的人物生活形式較為老派,想像了一個未被時間沖刷的北京中心,就像主人公們在老白家中看影片就好似如置身於烏托邦主題公園當中那般,的確與外來者飄蕩恐懼的生活幾乎毫無取得聯繫,但卻無法因而說自己的團聚就是偽善的,自己的眷戀就是虛假的。在真正凝聚了生活的具體物件與脫離生活徒有機殼的消費品之間,應當有公正的區分。即便,具體的物件是觀眾們理解人物的關鍵線索,也是透漏親情主色的詩意,的話又怎樣解釋張愛玲在《第一炉香》裡寫葛薇龍懷念北京家裡做鎮紙的水晶球,“嵌著細碎的紅的藍的紫的花,排洩俗氣的齊整的團案”,“家裡人給她捏著,冰那火燙的手”。類似於葛薇龍的玻璃球,俗氣尋常的東西也可成為富有生趣的詩意,與有著相近經歷的聽眾或觀眾們形成共鳴。
《爱情神话》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要點就在於閒話。老白家的畫室充滿著著學生的“嘎訕胡”(講閒話),Gloria是其中佼佼者,她交待了他們有錢有閒、老婆遇難、“千萬別太靈額”的中年生活。與陳女士的搭話較之,Gloria的閒話儘管幽默新鮮,確實少了許多值得琢磨的意思。老白進到陳女士家,陳女士的個性和情誼藉由若有似無的搭話透漏出來,陳女士爸爸在外邊高聲爭吵,老白覺得尷尬,說自家媽也是這種,陳女士只輕輕地說,“有撒好比?”這話用上海話講出來確實比廣州話更有味道,這一刻信息溝通交流反而比不上柔和吐露的姿態、充滿著體貼的證實關鍵。
現代人或許指出後一種生活儘管殘暴卻更“合乎現實生活”,飄在空中的文藝男性青年迴歸地面便是這時候,但唯美與現實生活的觸碰絕非一定要以彩色泡沫破滅為終局。能夠讓現代人上街買他們討厭吃的小菜,呈現出日子平平穩穩的樣子,或許還帶一點點唯美,而並非將改建所有人為同一個面目,號令閒話和補丁統統消亡,也許是觀看《爱情神话》的另兩層啟示。
“歡樂的這時候,無線電的聲音,馬路上的色調,好似我也都有份;即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淤泥。”
本報記者 | 董子琪
對影片主人公而言,這種長此以往地生活下去是可以想像的,自己的歡聚、別離、閒話、糾纏都猶如世情短篇小說富有節拍。這更是一種平衡的、富有周期感的、可以持續的生活——局中人相互知根知底,即使初次見面也能很快熟絡,形成一種輕鬆融洽的氣氛,即便是成為過去式的前夫蓓蓓也願意“軋鬧猛”回到席間。現代人時而總結人生實戰經驗,男人怎樣才算是完整的;時而探討現下生活,哪條苔條黃瓜、蜻蜓酥最美味。正因為那一刻好似可以一直綿延下去,老烏的逝世就可以成為電影的關鍵句號,而為的是逝世的相約同樣是生活中的週期性該事件,無須過於哀傷,現代人能夠攜帶著悲傷,繼續生活下去。
主人公的生活裡沒有什么大波瀾,老白三日主要行程如下:教人寫字,跟學生聊天,踏進家門去外貿服飾店買鞋子,去雜貨鋪採購肉類,最後去咖啡廳。打破常規日程的,自然是對陳女士居所的造訪。永和路185號門外傳來大提琴聲,他藉著送書的名頭,看見了陳女士不那么優雅神祕的內部生活——她和爸爸一同住,樓道里燈泡壞了,電阻老化怎么也修不太好,這天早上扭斷鞋跟的平底鞋擺到樓道的鞋架上,她的臥室促狹,擺滿衣裳,只有兩張小圓桌,牆面上貼的是孩子的識字圖。陳女士脫下那夜神祕而婀娜的的女神禮服,和爸爸即使隔夜菜和學費吵得一地雞毛,還要輔導筆試不及格的小孩做功課。陳女士教孩子默寫的單字——“冷靜、相距、生氣”——好似也是她個人掙脫不出去的感情困局。
このサイトは、映画のポスター、予告編、映画のレビュー、ニュース、レビュー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映画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す。私たちは最新かつ最高の映画とオンライン映画レビュー、ビジネス協力または提案を提供します、私達に電子メ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著作権©2017-2020 920MI)。メー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