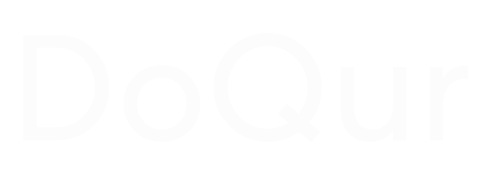千萬別輕易豎起你的中指!這恐怖電影已經告訴你後果了
為什麼是那三個變態陰魂不散,又出來作妖了?
什么感覺?
更難得的是,它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
其一,巧克力車裡的三個變態闖進老宅,被姐妹倆彪悍的父親整體實力反殺,隨即莎拉的夢醒了。
正當我這種腦補的這時候,第二處反轉來了——這一切都是莎拉的幻想。
以致於假如你想在觀影過程中揣測故事情節的走向,基本都會被無情打臉。
但是劇中大量的場景復古藝術風格十分顯著,但編劇對於陰影的巧妙運用又抬高了暖色的天然親和,反倒營造出一種年代久遠的清冷疏遠感。
最傷痛的是一直處在噩夢之中嗎?不,當你自以為總算逃出噩夢,卻又醒來只不過未曾逃離,這才是最傷痛的事。
而且莎拉從地獄回到世間,再重新墜入地獄的心態劇變可想而知。
該片能夠兼顧二者,著實難得。
那是不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呢?還真有。
瘋狂?凶殘?變態?但不可否認的是,不論聽覺還是心理,他總能精確觸碰到觀眾們的絕望脊髓。
——《噩梦娃娃屋》。
再比如說虛實交替的場景切換。
妹妹思想崩盤,自殘、神志不清、瘋狂尖叫聲,父親或許也隱藏著什么可悲的祕密。
如此認為,該片在聽覺和心理上多重滿足了觀眾們所需的恐怖感。
那么請你們閉上眼睛想像,當你沉醉於幸福幻想時,耳邊忽然響起一個聲音:你的妹妹已經被我們玩兒壞了,現在輪到你了。
本片的凶殘、壓抑程度,就算時隔多年仍然叫人心有餘悸,活剝人皮的場景,足有資格霸佔任何血腥臺詞駭人程度的排行榜前列。
最重要的是,以往我們看見的恐怖電影多半以聽覺驚嚇、刺激觀眾們的聽覺神經居多。
途中兩輛巧克力車經過,車主熱誠地向她們打招呼,莎拉友好澄清,維拉卻偏偏對人家豎起了中指。
英國血腥短篇小說大師史蒂芬·金曾說過:血腥片分成三種,一種是低成本的、一驚一乍的嚇人,另一種是高級的、入侵人心的絕望。
即使如此,也千萬別小看它,因為全劇所營造的恐怖感可謂是一趟心理上的地獄之旅。
實際上,父親已經慘遭毒手,姐妹倆也一直被三個變態軟禁煎熬,出於自我保護,莎拉一直活在他們的幻想裡,現在又被妹妹一巴掌打醒。
一邊以極端的姿態反覆拷問家庭、親子關係等傳統主題,一邊又有著與西歐表演藝術影片共通的個性,既有別於英式血液片的濃郁,也有別於日韓恐怖電影的焦灼。
而該片劍走偏鋒、另闢蹊徑,非但沒有嚴格遵守這一規則,反倒使用了雙故事情節線穿插描述、現實生活與虛幻交替上演的複雜技法。
該處巴斯卡·勞吉哈巧妙地藉助變態對洋娃娃的蹂躪預示著莎拉的境況,讓觀眾們一邊期盼,一邊又不忍心看見接下來的凶殘場景。
居然就是這種一個叛逆的行徑,竟成了姐妹倆一生最血腥的噩夢的開始。
變態人魔、怪異老宅、血腥虐殺,傳統歐美恐怖電影的俗套元素一應俱全,嗎很像上文提及的第二種低成本的、一驚一乍嚇人的中低端恐怖電影?
這是想表現父愛真偉大還是學我們國產恐怖電影的夢一場?僅僅過去一半的進度條啪啪打臉。
如此複雜的敘事形式非但沒有讓該片的節拍變亂,反倒成為了全劇最為出彩的地方。
全劇決定故事情節走向的反轉有三處:
前者求索於人類文明的本能,神經系統對於血腥場景的直接反應,後者則倚賴共情能力,稍顯複雜,負面影響也更為綿遠。
提起該片的編劇巴斯卡·勞吉哈,可能將我們並並非很熟識。
今天小嗨要和我們分享的整部,乍一看屬於第一種,實際卻屬於第三種。
故事情節的主角是兩對姊妹:姐姐維拉現實生活、叛逆,妹妹莎拉內向、想像力很強。
光憑小嗨乾巴巴的敘述我們可能將體會不到其中的涼意。
該片也不例外。
如果說直接看見恐怖場面是“來得痛快”的話,那么這種的“下一個是你”就是煎熬人心。
但對於他的處女作,想必恐怖片發燒友都不能陌生——《殉难者》。
比如說莎拉假扮洋娃娃的臺詞。
三個變態其中之一智力低落卻有著嚴重的暴力行為傾向,他將莎拉裝扮成洋娃娃的樣子與一大堆洋娃娃放到一同,隨機挑選出施暴,莎拉要忍住絕望、飾演無聲無息的人形才可能將逃過一劫。
虛實交替、一波三折,從這種充滿著創造力的總體架構上看,該片屬於很典型的“新比利時分裂主義藝術風格”的產物。
比皮膚受到禁錮更可怕、更可悲的是靈魂上的困局和恐懼,傷痛到來前的折磨遠比直接的傷痛更更讓人膽寒。
同樣受到煎熬的還有熒幕外的看客,如此一波三折的操作簡直無情。
兩人與父親一起開車,準備搬到近郊姨媽留下的老房子裡。
一般而言,傳統恐怖電影的故事情節一般來說簡單明瞭,即使過分複雜的懸念和線索極容易分散觀眾們的注意力,進而大幅度弱化觀眾們直觀接收到的恐怖感。
而相比之下,該片則更為著重心理上的煎熬。
即便許多人觀看恐怖電影就是為的是尋求刺激,聽覺衝擊無疑是最直接明瞭、直觀粗暴的表達方式。
千萬別輕易豎起你的中指!劇中的姐妹倆已經告訴你後果了!
このサイトは、映画のポスター、予告編、映画のレビュー、ニュース、レビュー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映画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す。私たちは最新かつ最高の映画とオンライン映画レビュー、ビジネス協力または提案を提供します、私達に電子メ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著作権©2017-2020 920MI)。メー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