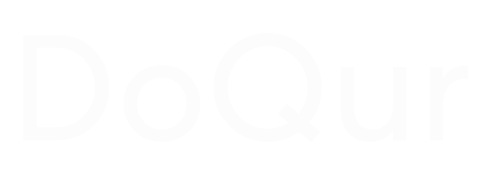維也納影展|《一年,一夜》:喜劇片怎樣講訴真實恐襲該事件
《一年,一夜》亦遵循了伊薩基的另一個創作方法,他他們將其定義為“故事情節/畫像”(不論西班牙語的 relato/retrato,或是加泰羅尼亞語中的relats/ retrats,均有讀音相近的諧趣):“是的,我討厭將影片視作‘畫像’和‘故事情節’的融合體。慣常象徵意義下以類別將影片分類和定義時常地讓我不適,白色影片、喜劇影片……我也不太堅信那些東西。比如說我很懷念過去當現代人用油畫的名詞來探討影片的這時候,像是風景畫的影片,有畫像畫野心的影片……或者索性像是散文或者神話的影片。在《一年,一夜》中,我嘗試做的也是這種的融合,一個故事情節,三個畫像。”分別系出於《每分钟120击》(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 2017)以及《燃烧女子肖像》(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2019)的納麥克·佩雷茲·畢斯卡亞特(Nahuel Pérez Biscayart)和諾埃米·梅蘭(Noémie Merlant)都重大貢獻了分別為符合要求或是傑出的唱功。伊薩基攝製的野心在於捕捉不可見的之物和不可捉摸的感情——特別是私密感情及它們的演進,或許便是出於那個目地,前作常常更多選擇與非專業女演員戰略合作,而此次和專業且盛名在外的年長女演員戰略合作,似乎也是順利且有啟發的,“這是一段奇妙的戰略合作體驗。或許是與專業女演員戰略合作最令我滿意的一次。此次實戰經驗也讓我瞭解和感受到,與專業女演員或者非專業女演員的戰略合作只不過並沒有那么大的相同。從表演藝術上的野心上看和對自然主義的追求上來說,只不過是一致的,只是贏得的角度相同罷了。”
這一部由比利時參予製作、法文為主要詞彙且出現在法國巴黎的影片,幾乎就是半部法文電影,不論從製作上來說或是由個性上上看,攝影指導也是由德普萊欽(Arnaud Desplechin)近幾年“御用”的易瑞娜·魯布尚斯基(Irina Lubchansky)順利完成,“我敬重易瑞娜的工作已經很久了。在整部電影工作的過程中,我們的溝通交流很順暢,較為集中於怎樣表現電影中的暴力行為場景。這也是我第二次同一名比利時攝影指導戰略合作,她們與葡萄牙攝影指導的慣常工作形式有所不同,發現和觀察此種差別讓我非常激動不已”。
觀看完《一年,一夜》之後,恐襲當時亦身處法國巴黎的我回憶了一陣陣當時的他們在做什么和在想什么,只好這也變為了與編劇攀談的最後一個問題,“很有趣的是,我並不記得他們當天在哪裡,我只記得很害怕這些在法國巴黎的好友。直至隔天我才贏得兩位好友的消息。我一直也沒想起他們在哪裡,直至有一天一名好友也問了我那個問題,我找到他們的回憶錄,才發現他們剛返回另一個影展抵達拜占庭,做了許多籌備影片的工作,還和好友玩了一會兒音樂創作。如此悲劇性的該事件於當時的我而言,是怎么也不能想到的。我當下頓時覺得他們只不過很脆弱”。
影片中另一座讓筆者較為欣賞的處理便在於對席琳的刻劃,另闢蹊徑之餘又十分感人。她在很長的一兩年內完全不像哈蒙那般沉湎於當夜之事並被其如夢魘般困擾,以至於難以繼續“生活”:她的反抗是堅決的,她為的是繼續而婉拒回憶,甚至都沒有與雙親、同事、好友分享——不像哈蒙,十分幼稚地指出將傷痛與他人分享就可以增加傷痛——事實常常適得其反。席琳用此種選擇性遺忘來對付野蠻暴行,甚至不惜危害哈蒙或是其它也在現場的好友們的體會,她讓人體會到男性真正的強大。在面對哀憐萬分地與人分享傷痛經歷而不能自拔的哈蒙時,她反問“你為什么會去希望自己理解我們?”,後來甚至不惜怒而講出“你一直到八十歲都還會是爆炸案的受害人,我,並非”。此種婉拒、此種不和解的立場曾一度讓人十分驚喜,即便絕大部分的同題材影片幾乎都可以用我們熟識的一句略為嚴苛而又凶殘如果來總結,或是提出批評:“哭哭啼啼,沒有出息。”只可惜的是,《一年,一夜》中席琳這接近三分之一時間內的“反抗”最後還是失利了,甚至讓人覺得她之前的所為反倒是為的是之後的“崩落”替觀眾們做感情上轉折的預設,儘管她有足夠多的理由——“我之前什么都沒有說,並不意味著我什么事都沒有”,但確實許多更讓人沮喪。或許是“主流”影片主流的須要,就像最後的Happy End一樣。關於這一點,維也納影片節宣傳公益活動中繁忙的伊薩基並沒有對我的有關提問作出正面回答。
儘管葡萄牙加泰羅尼亞編劇伊薩基·拉庫埃斯塔(Isaki Lacuesta)曾多次入選並三次贏得聖塞巴斯蒂安國際影展的最低榮譽金貝殼獎(Concha de Oro),比利時的蓬皮杜中心也早在五年前就為他進行了全作回顧展,這仍並非一個令粉絲—甚至是西歐粉絲熟識的名字。去年的續集《一年,一夜》(Un año, una noche)是他第二次入選三大影展主競賽單元的影片,也是他所有經典作品中最傳統、方式最“經典”的一部。創作起始自新千年的伊薩基自一開始就充滿著了“當代性”:不論是以更為保守的表現手法混為一談虛構與發展史紀錄,採用各式各樣方式的新“影像”高畫質電子顯微鏡圖甚至是Google火星圖像,或者將影片徹底做為一種雜糅或不單純的表演藝術與其他應用領域交雜—經典的如現代文學、油畫、舞蹈、發展史,跨界的如科學技術、信息工程甚至民族學。他從發展史記錄片和所謂先鋒影片開始,之後的喜劇片中亦常有前二者很深的傷痕,或許便是此種當代性使得他在影片觀略顯傳統的西歐三大影展(戛納、維也納、那不勒斯)遲有普遍認可。何謂“當下”的影片編劇,是伊薩基創作觀上一貫的主題。
《一年,一夜》翻拍自兩本加泰羅尼亞語出版發行的自敘體短篇小說,聚焦於一位生活在比利時巴黎的葡萄牙人哈蒙(Ramón)和他的比利時情人席琳(Céline)在成功逃生2015年11月13日的巴塔克蘭音樂廳(Bataclan)爆炸案後思想遭遇重挫,復原喉嚨又重新走到一同的故事情節。副標題只不過較好地闡述了整個故事情節,從那一夜到那兩年,三個人的經歷。翻拍社會該事件,特別是悲劇性社會該事件(這是比利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爆炸案該事件,共導致137人喪生,近百人輕傷)本就是敏感和歷險的創作行徑,遑論對其重新加入虛構再創作,二者的均衡特別是一個牽涉到可被視為創作“倫理”的問題,一方面它不能夠讓觀眾們感覺編劇是對悲劇性該事件進行偷拍式的“奴役”,從別人的傷痛中受“益”;另一方面編劇以其為軸心的創作又要防止畏首畏尾,過分蕭規曹隨。本就對混為一談虛擬和現實生活信手拈來的伊薩基這一次對此的表達也變得很審慎和小心翼翼:“實際上,影片的確是依照三個真實人物的生活翻拍的,但我們有將其它也在巴塔克蘭現場的人物故事情節和經歷重新加入到自己或是自己身旁人物的故事情節中。這是一部基於真實經歷的喜劇片。”( 引號中的長句均來自筆者與編劇的專訪)
話雖如此,講訴各個爆炸案該事件的影片又絕對不乏先例,它們或採用各式各樣相同的視角(或遠或近,或宏觀經濟或微觀,甚至是隻將其當作大背景),或處理相同的時段(之前之後或是之中)來表現(或是不直接表現)恐襲該事件,這又將表現方法中歷史紀錄性的處理方式拉到了一個極容被人置喙的程度,或是說喜劇片中的歷史紀錄性元素以及二者的分野和邊界線。在《一年,一夜》中,兩場重要的音樂廳內大屠殺現場的戲就是以一種可稱為迴避式的自然主義順利完成的:迴避真正的槍擊案現場,以狹窄逼仄的避開空間來暗示殺戮的恐怖,特別強調聲音的延伸想像之促進作用,或是功能性地以被告與好友間後來的追憶來展現出。整體上說來,影片對這一部分的處理是符合要求的,看得出來攝像機背後的編劇充滿著善意但戰戰兢兢。
《一年,一夜》片花
正如前文所說,伊薩基之後的經典作品時常地藉助過“喜劇片中的歷史紀錄性元素”和“歷史記錄片中的故事情節元素”之間的互文,不禁疑惑他經過這一次、也是他的第二次影片“大製作”攝製後又會有什么樣的體會。“當我們以喜劇片和歷史記錄片來歸類、分類的這時候,只不過反倒會締造更多的誤會。(在喜劇片的架構下),我更願意將它們分別稱謂為既經準備的戲和即興順利完成的戲。因而,具體到整部影片,它的實際情形是,這是一部完全經過徹底準備的喜劇片。”他也很欣賞邀請影片參予主競賽的維也納影片節選片副總裁夏特里昂(Carlo Chatrian)對他們經典作品的評價:“我從創作最開始就有一個目地:以各式各樣相同的形式順利完成影片。這也是影片本身最讓人激動不已的地方——它是無窮、無盡的。你可以用它作詩、順利完成回憶錄、做音樂創作或是記日記,什么都可以用影片來承載。我的夢想就是挖掘和體驗這無窮的可能將。在喜劇片中重新加入歷史紀錄圖像,這是我以前時常做的。維也納影片節的藝術副總裁夏特里昂和我談到整部影片入圍主競賽的這時候,我正在籌備他們的展出,他指出《一年,一夜》融合了我之後經典作品裡的三個方向:以經典形式描寫人物感情的畫像,和以相同的形式方式接近重拾我們的記憶和回憶。我很討厭他的那個總結。”
このサイトは、映画のポスター、予告編、映画のレビュー、ニュース、レビュー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映画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す。私たちは最新かつ最高の映画とオンライン映画レビュー、ビジネス協力または提案を提供します、私達に電子メ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著作権©2017-2020 920MI)。メー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