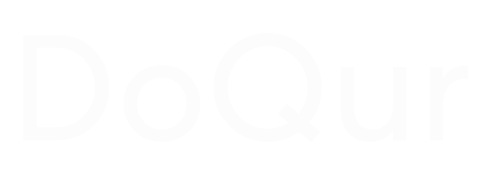“零零後”這一代很早就認清了世界的規則|訪談盛志民
而且,小博和子昭兩人的親情是模糊不清的,小博或許能夠取代子昭順利完成夢想。但這只不過挺殘暴的,在某種程度上,小博嗎子昭的一匹馬呢?(編者注:在《冲撞》中,子昭說他最好的好友是馬術課的一匹馬。)
南方週末:你說的“中間”是指兼顧商業性和創新性?
盛志民:我發現“零零後”這代小孩很早就認清了那個世界的規則,但,他們時常不曉得自己該怎么辦,他們就像困獸在籠裡橫衝直撞。對我們“六零後”這代人而言,當時我們存有著許多感情的進口,比如說搖滾樂和實驗話劇、獨立影片,社會還有很多的機率。
去年12月21日,《冲撞》在第16屆中國哈爾濱影展的“影譚”單元展映,在電影的映後座談裡,編劇盛志民和衛西諦再度進行了對話。此次,盛志民將攝影機對準了當下的青年人。正如劇名說的那般,喜劇片《冲撞》描寫了三個曲棍球少女的“衝撞”——這是社會階層、地域、價值觀和理想的“衝撞”。從記錄“六零後”“七零後”流行樂青年的彷徨,到《心·心》深入分析“八零後”女青年自主的性意識,再到《冲撞》“零零後”青年人的思想情況,隨著時代變化,盛志民企圖把握每一時代青年人在理想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徘徊,記錄下青年人最純真的表情。
以前,在傳統的舉國管理體制下,練球的小孩能從少年隊、青年隊一層層選為國家足球隊。拿了健將證後,他就可以保送上學院,上學院後的工作包重新分配。在市場化改革之後,我們可以選擇當職業選手,沒準還能去打NHL(北美地區的國家曲棍球聯盟),這直接打散原來的管理體制,也發生改變了曲棍球的業態。
盛志民的新劇《冲撞》是以中國曲棍球運動為大背景的青春片,跟許多人想像中的體育勵志片相同,片裡沒有“打怪升級”式的爽片套路,也沒有不斷煽情的“超燃”逆襲,更沒有“鯉魚躍龍門”式的魔幻結局,這是一部關於成長的電影。西北傳統體校練曲棍球的小博,走進了上海的曲棍球俱樂部踢球,與他的“富二代”球員出現了碰撞。在觀念、理想和世界觀上,小博與他的球員格格不入。此時,小博邂逅了隊中同樣愛好曲棍球的子昭,併成為了好朋友。自己在情意和價值觀念上的“衝撞”構成了影片最大的衝擊力。
籃球拍沒法,我們可以拍曲棍球。曲棍球速度慢、又有衝撞,規則還容許直接打架,這多漂亮!我把曲棍球那個概念給了一名年長編劇,編劇去西北考察回去後,寫了一個故事情節大綱。他的故事情節偏勵志方向,我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後來,那位年長編劇放棄了那個工程項目,但我對那個工程項目念念不忘。這可能將即使我是個體育迷,上過體校,是建業隊的球迷。在2017年和2018年的這時候,我趕上了中國電影熱錢的四肢,領到了投資。
南方週末:在《心·心》中,你可能將拍的是“八零後”的生活狀態,《再见乌托邦》拍的是“六零後”的生活狀態,現在拍的是“零零後”的生活狀態,你覺得這幾代人的生活形式和價值觀有什么樣的異同?你是怎樣跨越那么大的代溝,去理解當下少女的思想世界的呢?
影片行業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不依照規律性處事。每一編劇都有他成長的規律性,編劇必須自然而然地成長,而並非被一個機構、資本、綜藝節目等怪異的外力介入,強制發生改變他們的經濟發展路徑,那些外力事實上是為的是自己的自身利益。所以,很多編劇和那些外力形成了共謀關係。那個共謀關係發生改變了一個編劇的成長路徑,也發生改變了行業生態環境。我希望此種單純的外力能夠增加,編劇要通過自己的創作一點點以獲取資源,再贏得新的創作機會,而並非以一種運動式的形式來贏得經濟發展。
在2016-2017年齊齊哈爾舉行的曲棍球冠軍賽中,長春、齊齊哈爾、佳木斯和市場化改革的遼寧隊進行賽事。在遼寧隊與西北某支球會的賽事中,遼寧隊隊員學生家長們在現場高聲打氣,就像在NHL現場一樣,那群西北學生家長則在默默地看球,那個場景把我樂壞了。在這場賽事裡,一名遼寧隊的隊員還被打了,當然,曲棍球是容許按規則打架的,但自己肯定帶著氣打的。那個場景讓我決定要拍《冲撞》整部影片。我花了兩年時間,跟上海曲棍球俱樂部的學生家長們閒聊,也跟孩子們閒聊,我基本上把打曲棍球的上海小孩們都認全了。在這之後,我回去寫電影劇本。而且,《冲撞》中的許多事情都是真實出現過的。
《雄狮少年》片花。
盛志民:現如今影片行業最大的問題是愈來愈不多樣化。真正有他們世界觀和美學觀的作者是極少的。當年,賈樟柯、婁燁、王小帥都有他們獨立的世界觀和美學觀。現在,一位青年編劇,要么走影片節的路徑,要么與大子公司簽下。在影片節裡,大量青年編劇在功利的目地下創作,真正有自我意識的創作是不多見的。現如今最缺的影片只不過是類型片。《扬名立万》《误杀》《雄狮少年》《爱情神话》這種的類型片的電影票房之所以會起來,是因為我們太缺這種的國際標準類型片了。
南方週末:練曲棍球也算富足社會階層的這種素質教育。
《冲撞》片花。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 採寫:徐悅東;編輯:走走;校對:劉軍。熱烈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做為一位“六零後”,盛志民是怎樣跨越如此大的代溝,去理解當下青年人的世界的?在他對各代青年人的觀察裡,“零零後”青年人的精神狀態有什么樣的變化?對於中國影片市場而言,我們須要什么樣的青年編劇?趁著此次《冲撞》的放映,我們與盛志民聊了聊青年與影片。
《导演请指教》連最起碼對編劇的認同都沒做到
盛志民:這綜藝電視節目太可悲了。我可以公開地說,無論編劇拍得好還是不太好,都要贏得認同。影片是多樣化的,是該受到認同的。你無法為的是收視率噱頭而不認同編劇。那個綜藝電視節目連最起碼的認同都沒做到。現在,很多孩子稱自己是“飛機場”——這是畢志飛歌迷的中文名稱。他們之所以支持畢志飛,就是想抵抗電視節目中我們給畢志飛貼標籤的強權。
盛志民:對。小博帶著總教練的這句話走進了他的新世界——上海,結果他發現,那些“富二代”的邏輯跟他完全相同。上海的曲棍球俱樂部裡極為講“teamwork”,大家要懂得分享球。這其中埋著四條憎惡鏈:俱樂部的外教對子昭爸爸說,打曲棍球要“follow your heart”。子昭爸爸覺得老外的想法太直觀了——我們有我們野蠻生長的規則,別給我講“白左”那一套話術。“只有成功才有機會”的價值觀念和團隊戰略合作的普世價值觀念出現了嚴重的武裝衝突,這讓小博活得很擰巴。只不過小博不曉得,這四條意志完全是來自相同世界的規則。
盛志民:比如說,《扬名立万》裡有電影劇本殺的技術創新點,還合乎通常觀眾們的觀影習慣。因而,《扬名立万》能贏得市場電影票房上的成功。所以,電影市場最好還是要存有獨有電影的空間,但中間層是中流砥柱。現階段來說,中國電影市場並不處於最好的內部結構當中。但那些年我看見了許多變化,我們有了《扬名立万》《误杀》《我的姐姐》《少年的你》《雄狮少年》這種的中間層電影,年長編劇漸漸找出了一個適宜他們的經濟發展路徑。照著那個態勢,這種的電影愈來愈多,電影市場就能保持住。在電影市場保持住後,才可能將確保出許多獨特的影片。
綜藝節目《导演请指教》中的畢志飛。
在我剪完《冲撞》後,我總覺得還差一口氣,我就從虛構故事情節返回現實當中。光觀察是不夠的,在電影開頭,我把對女演員們的專訪放了上去,那些女演員的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境況,表達了我對真實的立場。我找了一個攝影師給自己拍照,讓自己敘述自己的青春。那個電影內部結構是相左常規的,可能將即使我體內還留存著這代流行樂人的混蛋勁吧!
盛志民:現實生活中有許多在俱樂部打曲棍球的小孩都很討厭打曲棍球,但他們非常清楚,自己在長大後不可能將繼續打曲棍球。在《冲撞》裡,在俱樂部打曲棍球的孩子們肯定愛好曲棍球,但他們很早就決定不踢球了。劇中有一名叫安德魯的女孩,他全身都穿著名牌。他說他們只不過都想成為職業曲棍球選手,但他曉得這是不可能將的,他踢球是為的是未來出國唸書能夠加分。
南方週末:我專訪《小伟》編劇的這時候,他曾跟我說,他很羨慕比利時的編劇,即使比利時有許多這種的小品。
現如今,資本顯得清醒了,影片觀眾們是用腳投票表決的,電影票房是難以操控的,市場環境是公正的。中國有個厲害的地方在於,影片公映那天口碑就出來了,觀眾們有他們的判斷。一部影片的電影票房就算賣得不太好,要么是口味小眾,要么是拍得不太好。現如今,作者影片實在太捲了,我覺得許多的作者影片本身就不合格,攝像機是不能說謊的。近年來的作者影片中,我較為討厭《小伟》,我覺得編劇很真摯。
採寫 | 南方週末本報記者 徐悅東
“不惜一切地贏vs團隊協同”三種價值觀念背後,
南方週末:你此次為什麼會選擇攝製體育青春題材的影片?為什麼考慮拍曲棍球那個題材?你是怎樣瞭解那些打曲棍球的孩子們的生活的?
有許多學生家長送孩子打曲棍球是為的是鍛鍊身體自己的個性。這些有錢人曉得,世界是殘暴的,自己得讓自己的孩子自小有能跟人打架的勁兒。這話是某一曲棍球隊學生家長親自跟我說的。
我們的編劇太美好了。只但,全世界的表演藝術片都沒人看,比利時也一樣,只是比利時政府出錢扶持表演藝術影片。我覺得自己沒什么可羨慕的。但,比利時會有許多影片院,理事長線地放許多表演藝術片。
在領到投資之後,我他們去西北考察。我幾乎認識西北曲棍球隊的全數孩子。當時全中國就四個曲棍球隊:長春、齊齊哈爾、佳木斯。這四個隊屬於國際標準的舉國體制。那時,上海開始發生曲棍球俱樂部。當時還設立了五傢俱樂部,希望能借以體制改革,推動中國曲棍球的經濟發展。
盛志民:不只是純粹,當時我們沒有那么卷。主要是現在的小孩太捲了,要反抗的東西比我們那時多多了。那時,我們這幫人覺得錢不關鍵,生活得自由自在就好。只不過,青春永遠是純粹的,但現在的小孩要面對的壓力和束縛真的是太大了。
南方週末:自己的世界觀是優勝劣汰的,要用一切方式往上爬。
南方週末:據你對當下中國青年影片的觀察,你覺得中國青年影片人的經典作品大體上呈現出一個什么樣的面貌和個性?你會希望更多什么樣的影片發生?
“零零後”很早就認清了那個世界的規則,
這回看見盛志民,他仍然一身素色裝扮,儘管年過半百,但他內心深處仍然是個熾熱的流行樂青年,“好玩兒”是他口中最常發生的詞。生於1969年的他早年玩過流行樂,跟孟京輝玩過先鋒戲劇,跟賈樟柯和陳果拍過影片。2002年,他拍出影片長篇小說成名作《心·心》。2006年,他的影片長篇小說《浮生》入選洛迦諾國際影片節。他在2008年攝製了流行樂樂記錄片《再见乌托邦》。後來,他與甯浩共同開啟壞兔子七十二變計劃,成為七十二變計劃核心編劇,並挖掘出了文牧野等優秀青年導演,面世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我不是药神》。
初次見盛志民,是在2019年冬天。他穿著白色T恤,戴著黑框眼鏡,指甲花白,卻沒有一絲蒼老的感覺。在馬路上,他也許會被自己錯認成坂本龍一。在中國流行樂樂記錄片《再见乌托邦》二十年重映的映後分享會後,他與影評人衛西諦回顧了中國流行樂樂的變遷史。正如劇名說的那般,《再见乌托邦》記錄了千禧年前後中國第二代流行樂人如竇唯、張楚和何勇,他們在商業、網絡浪潮衝擊下的茫然和無措。
當時,有一個很相似《棒!少年》的影片工程項目。在上海城西,有位籃球總教練招了許多打零工子弟組了個籃球隊,自己的籃球隊一路打到了英國。當時,那個工程項目在一間影片公司手裡。我跟自己說,最好的體育片來自“true story”,英國的很多體育片都是依照真實該事件翻拍的。後來,那個工程項目沒能繼續戰略合作,我們不了拍籃球題材了。
《冲撞》中西北體校出現的這些事情都有真實原型的。在《冲撞》中,西北的農村基層總教練告訴小博,世界只記得入球的人,不記得傳球的人。這是總教練人生中最後知道的道理,這也是他淪落為農村基層總教練的其原因。他覺得小博是好苗子,因而要告訴他,一定要抓住一切機會射門,千萬別給自己做嫁衣,只有這種,你的人生才有機會贏。只有不惜一切地贏,小博才有機會獲得全世界。這是底層對世界的觀點,也是他們的成功學。若他們贏沒法球,他們就什么也並非。
正所謂“現實生活具備熱火萬鈞之力”,《冲撞》歌劇上流露出來的真實層次感,讓這股衝擊力顯得更強,也讓人物極具震撼力。在我個人對華語影片的第一印象中,這也許是描寫所謂的“富二代”族群形像最真實的影片,沒有很多國產電影中對富足社會階層不切實際的意淫和刻板第一印象。在專訪中,盛志民提及,在滄州阿那亞放映之後,有位來自上海昌平的男孩非常感謝他,即使她覺得總算有一部影片能不偏不倚地把自己那個族群搬上大熒幕。
盛志民:曲棍球日常體能訓練是很貴的。對於子昭而言,他有許多條路可以選,但對於小博而言,他要徹底擺脫他的宿命,就只能成為曲棍球明星。子昭也想成為曲棍球明星,他跟家中為他做的選擇做對付,但最後他也拗不過父母。
日前,影片《冲撞》在哈爾濱影展展映。編劇盛志民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深度參予中國流行樂、先鋒戲劇和獨立電影的黃金歲月,對青年的思想情況有著精細觀察。從《心·心》到《再见乌托邦》,再到《冲撞》,他的攝影機下,“零零後”的青春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
《冲撞》這種的電影一定並非主流的,真正的主流電影必須在國際標準類型片的框架下創作,還兼具一定的創新性。我覺得《雄狮少年》尤其有趣,這是一部故事情節非常套路的電影,但它有非常新穎的地方——在國漫中,我們極少能看見聚焦於底層,還是東莞的自然主義題材。我希望相似《雄狮少年》這種的中間層的影片能愈來愈多。
《再见乌托邦》片花,何勇。
我覺得《冲撞》這個選擇題本身就很有流行樂勁兒。我們這代人被流行樂樂砸了屁股,流行樂是騙沒法人的。我不曉得我為什麼老拍孩子,可能將少女表情裡,總有一種東西能打動我。我拍《心·心》是因為那個時代的“八零後”男孩對於皮膚的自由掌控讓我尤其憤慨。她們可以選擇睡你,但她們睡你並不代表她們被凌辱了,而是她們他們的選擇。
南方週末:你才剛說的“六零後”,生長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可能將還有較為純粹的環境,而且相對較為純粹許多。
在我拍《再见乌托邦》的這時候,我回顧“六零後”和“七零後”的青春。這個這時候,我們還在追求烏托邦,後來商業和市場發生改變了我們的宿命。何勇現在還在精神病院裡。2009年,何勇拍著自己的後背說,我那兒的東西出不來了。那時,何勇時常說,我要賣彩玲,但錢沒有給到我。《再见乌托邦》中的一個孩子說,我也要賣彩玲,我簽了一間獨家代理子公司,但子公司沒有宣傳。何勇他們不懂的EMI商業邏輯,卻能在一個孩子嘴裡被輕易講出。
南方週末:你看《导演请指教》了嗎?怎么評價整部爭論很大的綜藝節目的?
南方週末:不曉得可不可以這種理解,男一號子昭儘管富有,但他是真正愛好曲棍球的。
兼顧技術創新和商業性的“中間”層影片越多越好
當子昭決定放棄曲棍球的這時候,他的溫柔夢想就遷移到了小博的頭上。儘管小博略有抵抗,但還是接受了子昭的饋贈(編者注:為的是小博能打首發,子昭幫他換了總教練,並幫他出國體能訓練)。小博終究還是“跪”了,即使他不“跪”,他的夢想是沒戲的,這一“跪”也讓這三個女孩順利完成了從少女到青年的成長——自己接受了那個社會規則。小博的好友早已經很熟識商業規則了,曉得怎么靠曲棍球賺錢。子昭自小的基礎教育也早早讓他知道那個世界的規則。小孩們會問,你們不曉得爸爸媽媽送你來那兒是做什么的嗎?你們以為你們真的能去NHL嗎?這群小孩對現實生活只不過是很清醒的。通過那個影片,我希望拍出這一代“零零後”青少女的生存狀態。
盛志民:這要從壞兔子七十二變計劃講起。文牧野、申奧、女王昭、曾贈、荒漠都是我幫壞兔子找的。2015年,我去中央戲劇學院做金字獎的評委,我在那看了許多年長編劇和導演的影片。我發現有兩個年長導演拍得尤其好,當時就推薦給一間電影子公司的老闆娘說,“咱們做點新導演的工程項目”,那時便是IP流行的二十世紀。在子公司的內部會後,我給自己放了文牧野的《battle》、申奧的《我不勇敢》,但自己並沒有什么反應。一兩天後,我給甯浩看了那些影片,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做壞兔子七十二變計劃。
我希望年長編劇能在那個環境中選擇他們的公路,這能夠多樣中國電影市場的多元創作。中國電影市場夠大,但是現在還沒有什么“木板”,年長編劇還是有機會的。
《冲撞》片花,子大正他的馬。
《冲撞》片花,小博。
盛志民:在比利時,一個年長編劇從第二個影片到第二個長片的平均值間隔是二十年。一名年長編劇要入行,基本上要拍兩部影片。但是,這兩部電影都要贏得國際A類影展的普遍認可。同時,自己還要持續健全長片電影劇本,這種就可以領到投資。
《冲撞》片花,主角小博。
タグ 浮生 誤殺 心·心 揚名立萬 我的姐姐 少年的你 再見烏托邦 小偉 我不是藥神 衝撞 battle 導演請指教 我不勇敢 棒!少年 愛情神話 雄獅少年
このサイトは、映画のポスター、予告編、映画のレビュー、ニュース、レビュー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映画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す。私たちは最新かつ最高の映画とオンライン映画レビュー、ビジネス協力または提案を提供します、私達に電子メ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著作権©2017-2020 920MI)。メー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