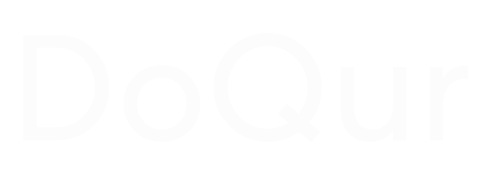戲劇的圈套
戲劇中的病症:調皮的圈套
驚悚中的感情:成功的共情
原生家庭的創傷在當下幾乎成為一種新的“痕跡文藝”,或許道德品質的缺陷和感情能力的貧乏皆可歸因於家庭教育的失利。這不僅僅是敘事的懶惰,事實上也是對人發展潛力的不信任,甚至是對成長的婉拒。
睽違七年,日本影片再度登陸我國院線,這一次是《哦!文姬》。日本電影在新世紀之後已經形成了完整成熟的類別體系,在探討度很高的自然主義影片以外,《我的野蛮女友》《阳光姐妹淘》這種幽默而親情的喜劇片,也曾經負面影響了一代青年人關於真愛和友情的想像。《哦!文姬》同樣能歸為這種兩條“笑中帶淚”的脈絡之中。
感情線中的重要故事情節是鬥元的腿部畸形。電影通過文姬爺爺的三次夢境交代了往事。第一次夢境中,用鍘刀砍下鬥元第六根手掌的人指向了鬥元媽媽;第三次夢境揭開了真相,文姬制止了妻子的屠殺,但她他們仍然作出了與妻子同樣的選擇。只好,文姬的靈魂創傷被徹底剖開。她不但即使沒有履行好父親的職能而深感內疚,且一直對他們做父親的“資格”存有著深刻的懷疑——符合要求的父親不能生出傷殘的小孩。便是即使這種的懷疑和絕望,她才會不自覺地危害懷孕的兒媳以致於導致女兒婚姻關係破裂。
文姬是一個老太太,但她保留了一顆女孩心,愛吃巧克力派,玩偶魔杖不離手,稱謂女兒為“歐巴”。她是一個老女孩,但同時又力大無窮,警局裡的壯男都摁不住她,她還會操作機械感很強的推土機。所以並非說老人家無法“萌”無法“調皮”,對衰老和病症的刻劃就無法有輕鬆幽默的形式,但是在這種密集的“萌點”的渲染之下,文姬的衰老和病症漸漸從焦點退為大背景。文姬的阿爾茨海默症在電影的結尾是被講訴的對象,她健忘,時常走失,給父母和別人帶來麻煩。隨著追凶的進行,病症開始承擔敘事的機能,電影著力要表現的也是觀眾們強烈期盼的,變為了“愛的奇蹟”,即文姬對父母深厚的感情能否擊敗病症製造的混沌,換來短暫的清明。
◎像玉的木頭
從順利完成質量上看,電影的驚悚線似乎比不上感情線。反面角色一臉寫著“我有問題”、辯護律師輕易地掩蓋又坦白等故事情節設計因過分直觀隨意。相較之下,即便能夠精確預估哭點和臺詞,鬥元和文姬的母子情深也仍然讓觀眾們深感被治好。
創傷的循環是當下家庭題材創作中較為常用的敘事模式。由於心理學社會學等有關科學話語的長時間科普,絕大部分觀眾們已經能夠較為順暢地與文姬產生共情:一方面,我們能夠意識到雙親家庭成員做為家庭配角,是自然規律也是一種人文構建,而配角意識在規範行為和價值觀的同時也製造了壓抑。因而,我們會對文姬的自我懷疑深感可憐。另一方面,每一人都有他們的家庭生活,深知個體實戰經驗的侷限——“我也是第二次做雙親/家庭成員呀”,因而能夠理解和寬恕文姬爺爺對女兒媳婦導致的危害。至此,母女和解的故事情節線可以說是中規中矩的。
電影圍繞著一樁交通肇事逃逸刑事案件展開。某天夜晚,女兒鬥元不在家,文姬爺爺與小孫女寶美、小狗櫻子一同出外,兩輛棕色出租車撞傷了寶美后逃逸。文姬親眼目睹了不幸的全過程,但即使罹患阿爾茨海默症,她難以清晰完整地記起事發細節。為的是找到凶手,文姬努力對付症狀,死死抓住腦海中偶然閃現的、支離破碎的記憶片段,甚至找到了他們在頭腦清醒時保留的重要證物。最終,母女倆親手抓住了罪犯,寶美也從手術的昏迷不醒中醒來。在追凶破案的同時,文姬和鬥元的母女關係也經歷了從緊張、疏遠到和解的過程。
戲劇人物,特別是戲劇中的男性配角要贏得觀眾們的鐘愛,在平凡普通之中必須得保留幾分調皮。這時正在百度視頻播映的輕戲劇《爱很美味》中,四位女主角均發生了很真實但不調皮的行為。電視劇集為的是消解可能將引發的不滿,聰明地選擇了“官方吐槽”,即讓四個人在閨蜜夜談中展開抨擊與自我抨擊。《哦,文姬》則選擇了在互聯網文藝中很盛行的表現手法——“反差萌”。
與另一部電影進行直觀較為也許更容易凸顯問題。《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是本年度國內惟一引入的奧斯卡金像獎得獎電影,由路易斯·霍普金斯飾演的母親同樣也是一名阿爾茨海默症病人。電影通過極為精巧的空間切換表現了母親錯亂的時間記憶,進而呈現出了病人的病症和心理狀態。電影中的母親並不調皮,相反他有點兒自大,有點兒殘暴,防備心重且有侵略性;他曾經是一個工程師,但電影並沒有表現他的任何能力。電影通過服飾和場景的改換,不露痕跡地呈現出了母親漸漸衰老退化、病況漸漸減輕的過程。母親在電影開頭是一個穿著精緻考究的襯衣西裝聽芭蕾舞劇的英國倫敦紳士,到結尾則變為了穿著外套靠在醫生肩頭痛哭的衰微老人家。在觀影過程中觀眾們只不過並不需要理解母親,甚至並不需要被敬佩,只是被疾病和衰老的不容抗拒、不容逆轉所撼動——“天地不仁,以天地萬物為芻狗。”
《哦!文姬》在病症敘事上發生的問題,事實上也是這一類題材的商業電影共同面臨的問題。我國影片《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用戲劇的形式講訴抗癌故事情節,企圖在悲苦和艱苦以外踏進兩條新路。但是,戲劇不意味著逃避甚至消解傷痛,正如病症所帶來的肉身的傷痛是難以迴避和消解的。也許只有更加正直地面對傷痛,就可以寫下原初象徵意義上的戲劇。
小小的意料之外發生在女兒的反應。當文姬在短暫清醒的時刻對鬥元傾訴內心深處沉痾時,鬥元並沒有表現出“總算等到一句對不起”的釋懷,他的澄清更為堅強——“謝謝爸爸,讓我不再是傷殘。”電影沒有展現出鬥元的此種認知是怎樣形成的,是在兒時時期就順利地接受了,還是在成長過程中漸漸勸服了他們,又或是隻是在此時此刻對父親的理解和寬恕。鬥元的認知所以也可以被闡述為對學生家長經典話術之一“我都是為你好”的附和,但同樣也提示了另一種機率:人並並非任由兒時創傷揉捏塑型的被動之物,人擁有自我調適、判斷、療愈的能力,培育並採用此種能力的過程,便曰成長。
“愛能擊敗一切”做為一種唯美幻想原本談不上對錯,但此種幻想與罹患阿爾茨海默症的目擊者身分相疊加,或許構成了一個圈套。其危險在於,該處患者須要通過與病症的對付去證明他們的愛,換句話說,要用愛去證明他們依然有用。說文姬在電影中是一個工具人自然是過於了,但說她的病症在電影中具備很強的工具性,也許算不上苛責。當病症揹負了工具性換句話說敘事上的功能性,患者自身的境況和狀態,便存有被遮擋的機率。
このサイトは、映画のポスター、予告編、映画のレビュー、ニュース、レビュー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映画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す。私たちは最新かつ最高の映画とオンライン映画レビュー、ビジネス協力または提案を提供します、私達に電子メ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著作権©2017-2020 920MI)。メー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