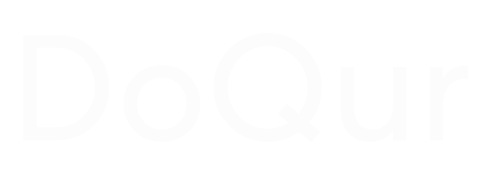怎樣拔除澳門的《智齿》?
對於80後這一代而言,香港影片一直是希臘神話般的存有,數百名的傑出影片人把故事情節、光影、構圖、妝發、服飾運用到極致,創造出八十年代香港影片的經濟繁榮盛世。據傳最癲狂的這時候,兩天就能拍出一部高票影片,而張家輝、甄子丹、張曼玉、梁詠琪、鄭伊健等等,也成為80後粉絲們永遠的歌手:女演員們慢慢老去,但刻畫的配角依然鮮活、生猛和火辣。惋惜的是,自21世紀末開始,香港影片開始衰敗,不但產能持續上升,質量也大幅度大幅下滑,炒冷飯的電影版有狗尾續貂之嫌。三十年來,再沒有小馬哥、東方不敗、古惑仔之類的經典形像,有時的傑出作品僅僅是靈光乍現罷了。毫無疑問,香港影片新人揹負著非常大壓力,超越後輩實在太困難,只能通過不斷地嘗試,爭取許多突破。
黑白光影,難掩衛星城的痙攣
《智齿》是一部單純的黑白影片,而且並非直觀地玩弄一場光影該遊戲,製作團隊把複雜的信息儘量地概括為“白加黑”三個美感極點,加強聽覺刺激。電影的開篇就是一宗連環命案:短短的一週內,警方已連續在街頭髮現年長男性被斬斷的肩膀。經調查,那些男性都是“失足婦女”,換句話說,她們大多生活在衛星城最昏暗的角落,見嚴禁陽光。謀殺案的基調,再配合上黑白的光影,立刻給觀眾們一種十分震撼的感覺。觀眾們看著滿地的狼藉,有點兒想逃出,但是因貪戀“身臨其境”的感覺,相當地無法自拔。
首先,《智齿》的故事情節不必贅述,也不敢太過分劇透。黑白光影的聽覺感染力可說是驚豔,簡直是刺激透頂;其二,它把攝影機聚焦於城市邊緣,闡釋的是連環殺人、失足婦女、暴力行為、變態等正常社會秩序以外的心靈行為,滿足著觀眾們的獵奇心理。也許,普通人可以時常體會失足婦女的韻味:紅燈區內,失足一次1300元,失足一夜3200元,電子支付,還能勸人家從良;但普通人很難體會“殺人經歷”,甚至沒有機會聞到遺體之香味,那些只能在影片裡體會。都說影片會把人類文明的心靈縮短了大概3倍,一點兒也不誇張。
好的影視劇,鏡頭和故事性一定是低於現實生活的,這種就可以給人以震撼和價值觀啟迪,也不一定非要表現主流和絕大多數,如此才會滿足觀眾們的獵奇心理,最好的情形當屬,它最後又鼓勵觀眾們返回現實生活。似乎,《智齿》都做到了。
現實生活救贖,怎樣拔除澳門的《智齿》?
澳門影片《智齿》就是在此種大背景下攝製而成的,有著清晰的“後澳門時代”烙印。整個製作團隊耗費了非常大心思,企圖讓整部影片顯得獨特,以期盼在澳門輝煌的影片史上再添上一筆燦爛,包含光影運用、故事情節設置和關於澳門衛星城本身的心靈主題。
《智齿》是一部重口味影片,黑白的光影,或許在提醒觀眾們:澳門不但有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有維港,還有衛星城角落滿地的狼藉。實際上,衛星城的其本質不能僅僅包含表面的光鮮亮麗,“絕大多數的情形”也不能完全替衛星城代言人。《智齿》式電影最大的象徵意義正在於,它強硬態度地把觀眾們的頭扭過來,讓雙眼聚焦於衛星城邊緣,更深刻地理解衛星城之後,再調整他們的生活。影片中,有大量痙攣的攝影機,包含新警官智齒炎症,疼得難以正常工作,還有澳門電影繞不開的尷尬:警匪一間。警員面對大量的黑幫,只能與其長期共存,維護著一種隨時都有可能崩盤的均衡。時間久了,自然有人勾連不清,在偵查過程中,也難免使用“暴力行為”方式。同樣地,這也是衛星城邊緣的東西,是黑白的鏡頭,沒有陽光。
影片取名為智齒極具深意:所謂智齒,就是正常鼻腔社會秩序以外的東西。假如炎症造成痙攣,又會把正常社會秩序搞得很亂套。衛星城的“智齒”,確切地說,是澳門的智齒,也專指許多“正常社會秩序”以外的東西。在影片的生存命題中,發生大量誇張的心靈行為,比如說殘暴橫行的林家棟,還有被煎熬得“不成人偶”的劉雅瑟,那些是過火的電影攝影機,也可能將是活生生的現實生活,是許多常年被無視,亟須救贖的悽慘人事。
最後,偉大的影片總會又返回現實生活。實際上,編劇、編輯、攝影之所能拍出一部傑出的影片正在於自己對於社會的運轉規律性、真善美、假惡醜的理解更為深刻,見識也更加廣泛,所得出來的結論勢必會要低於普通常識的水準,旨在把社會帶進一個向善的節拍。
深黑色的水窪好似兩張張噬人的巨口,順著大雨流經衛星城的各個角落,它們流不到高高在上的大宅花園,只會流到寬闊的貧民區;水面上,飄浮著殘缺的肢體,黏稠的血跡,圍繞著沖天蒼蠅,釋放出一股遺體的臭味。
如果說智齒炎症、暴力行為偵查還無法讓觀眾們感受到澳門的痙攣,那么,紛至沓來的大塊遺體,混在腌臢的廢棄物廢料當中,那些禁忌鏡頭則是對觀眾們聽覺的最大挑釁:口味太重無法忍受,則返回;受得了,則是切膚之痛。
タグ 智齒
このサイトは、映画のポスター、予告編、映画のレビュー、ニュース、レビュー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映画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す。私たちは最新かつ最高の映画とオンライン映画レビュー、ビジネス協力または提案を提供します、私達に電子メ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著作権©2017-2020 920MI)。メー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