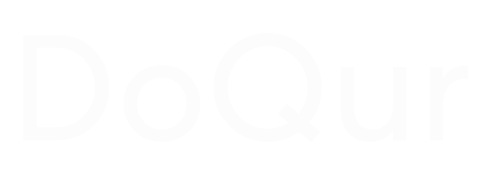整部“奧斯卡金像獎遺珠”,用了一種“新詞彙”|《波斯语课》影評人
在人性善惡分界的模糊性處理上,科赫成為人物典型。科赫的上場初第一印象是暴虐的納粹黨軍人,但隨著“專業課程”的順利開展,他在“親情”中展示出脆弱的另一面。在自我定義中,他指出他們只是個大廚,重新加入納粹黨的動機也只是在街上看見這群人很威風。
作者:初號機
也許沒那么刺激,卻餘韻悠長。
編輯:批量生產機
一般來說而言,一門詞彙常常寄託著對家國故土的悲傷與感情。《波斯语课》中,這門“詞彙”固然虛構,採用之人僅為主人公二人,但在本該導致“隔閡”的屬性中築起求生之路。一方面,雷扎從族群清洗中活了下來;另一方面,當內戰完結,雷扎所記下的2840個姓名傳達至了德軍手裡,不但成為同胞遭受迫害的證據,也令那些默默地被抹除的人生被人凝望。
除此之外,主人公雷扎也是在“平庸”設定下,隨著故事情節前進展現出了一個實時“昇華”過程。他在戰俘營的工作是浴室幫工與“阿拉伯語學生”。最初是為的是活下去而不斷緊張地捏造單字,對於外部世界帶有麻木的意味,但隨著接觸到愈來愈多的同胞,他對於納粹黨舉動有了更為清晰的憎恨。
從雙方人物的走向上看,《波斯语课》的反戰主題仍未直給,但暗含於看似庸常的一次次人際交往中。
全劇,雷扎的轉變也是靜悄悄的,而當他決定讓“救命恩人的哥哥”替代他們獲得活下去的機會時,他站在窗外看到日頭升起,那個暗喻事關個人與宿命,內戰與和平。
做為一部依照真實該事件翻拍的電影,《波斯语课》的核心設定足夠多“傳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一名猶太人在戰俘營謊稱他們是拜占庭人以期保命,恰巧一名奧地利軍人想要學拜占庭語,猶太人藉助戰俘營中拘禁的同胞名字做為單詞,硬生生“締造”了一門詞彙,而軍人在一堂堂“拜占庭語課”中對那位猶太人造成了倚賴……
科赫用“阿拉伯語”寫的詩
戰俘營裡的“勞作”
“猶太人犯人的名字締造了一種新的詞彙,納粹黨軍人用它寫下一首歌關於和平的詩。”
從故事情節大力推進上看,為的是圓謊、求生,一連串“債務危機—化解”設置為故事情節平添了波瀾。
科赫的經歷就因這門“阿拉伯語”而發生數個極具嘲諷意味的因果循環—— 他曾反問雷扎為什麼要和“無名之輩”一同送死,但他們平日裡兢兢業業自學、唸誦那些“無名之輩”的姓名。那些被拆解的名字成為他想像中的雲朵、希望、心靈,他藉助受害人的姓名作詩,用這門“迷人”的詞彙傾吐他們隱藏的過去。
這部電影圍繞著主角們的“日常”生活而展開,對於內戰的正面描繪大多存有於寥寥幾幕中:遠景、全景攝影機中的槍聲與倒地不起的人影,最簡單的也但是對於受害人赤裸屍體的一場俯拍。 全劇兩半小時幾乎沒有淚點,僅在開頭雷扎顫抖著誦讀2840個名字時,觀眾們累積的情緒獲得了一個小小的傾瀉口。
在略顯疲弱的四月檔期,市場上有重映的《阿凡达》佔足噱頭,也有兩部新劇登陸院線。其中,3月19日公映的《波斯语课》日電影票房排行漸漸走低,也在同期評價最低——豆瓣打分8.3。
在圍繞本片的眾多消息中,常被提到的一詞是“奧斯卡金像獎最大遺珠”。其原因在於,整部多國戰略合作順利完成的電影因主創人員團隊雙重國籍問題,無緣奧斯卡金像獎競逐。
主人公在被運到戰俘營的馬路上,用幾塊香腸換來兩本阿拉伯語書,這兩本書陰錯陽差地成為他是拜占庭人的佐證,同時賦予了他“雷扎”的名字;當雷扎為生造詞語而傷痛時,正好注意到他們謄抄的猶太人名單,從名字中吸取靈感;當戰俘營來了一名真正的拜占庭人,一名受過雷扎幫助的人為報恩而槍殺了拜占庭人,挽回了雷扎的祕密…… “雷扎與否會被揭穿”的懸念促進故事情節前進,造成了正確的觀看節拍。
在戰俘營中,圍繞“阿拉伯語”進行的求生環節以外,劇中有十分一部分內容在於納粹黨僱員間的“辦公室政治”。科赫做為掌理戰俘營餐飲等後勤保障外交事務的軍人,每日在辦公室困惑的是女助理畫畫太潦草、他們背單詞進展不夠快。 而將視角延展開,一眾納粹黨僱員的職場生活,也在“普通日程”中淡化“劊子手”標籤的獵奇感。
此種“內斂”的設置,意味著反戰主題在劇中是隱含的。但相較於簡單的殘暴鏡頭,對於“日常性”的側重刻劃,也許在回憶起時更能夠更讓人毛骨悚然。
較之於內戰的恐怖,人性怎樣刻劃可能將更加難於。
現階段口碑上看,《波斯语课》讚譽較多,但也不乏批評。無論如何,《波斯语课》依然在一定水平中帶來了一場兩半小時的靈魂拷問,也許沒那么刺激,卻餘韻悠長。
雖然大獎上有惋惜,播出關注度也不太高,但對於許多觀眾們而言,整部第二次世界大戰題材影片值得兩張電影票。以一名高贊評價為其總結——
戰俘營裡,被燒燬的猶太人名錄
“日常工作”
詞彙,謊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題材中,不乏角度新穎的佳作,但圍繞“詞彙”、在雙重隱喻下的操作依然為《波斯语课》帶來新意。
在對整部電影的評價中,有一點具備一定爭論——對於“反戰”故事情節的刻劃,也許“不夠多”。
總編輯:依梧
攝製電影時,編劇找來社會學副教授,採用猶太人死難者的名字,締造出了劇中的“阿拉伯語”——這令電影本身蒙上了兩層更加沉重的陰影。 在血淋淋的事實之下,這門虛構的“詞彙”寄託著雷扎的求生,甚至也投射著納粹黨軍人科赫能稱得上樸實的夢想——他希望內戰完結後去巴格達開餐廳。劇中或明或暗地特別強調“詞彙”的力量,如戰俘營絕大多數這時候是晦暗的冷色調,但一盞檯燈點亮的“阿拉伯語課課室”總是充溢著暖融融的氛圍,照出人性幽微與“友誼”滋生。
人物中,有千方百計追求同事的中年男子,有不敢去浴室幫工的女助理;故事情節上,有青年男女愛情的試探和困惑,有在背後取笑上司被打小報告的勾心鬥角,有全員散步、聯誼的“團建”……就是在這日復一日宛如正常辦公場所的戰俘營裡,更襯托出了人性之惡的“如常”——犯人的生死能是賭注的一環,煎熬是調味料,一切舉動都在“工作”的要求中井然有序地進行。
このサイトは、映画のポスター、予告編、映画のレビュー、ニュース、レビュー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映画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す。私たちは最新かつ最高の映画とオンライン映画レビュー、ビジネス協力または提案を提供します、私達に電子メ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著作権©2017-2020 920MI)。メー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