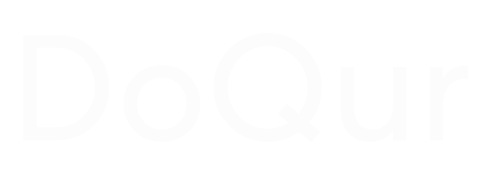《波斯语课》:阻擋平庸之惡的槍械
《波斯语课》最妙的一筆在於雷扎的“造詞法”。為的是不致在科赫面前露餡,他將戰俘營裡猶太人的姓氏與名字拆開,做為他自創的阿拉伯語單字的讀音,並以荷蘭語注音符號,傳授給科赫。一個個平凡的猶太姓氏與名字,成了“樹”“肉”“湯勺”“椅子”……這樣一來,單字代表的實物與猶太人的名或姓形成對應關係,也就是社會學上的所指與能指融合,構成了語法。
《波斯语课》片花
除了主題的探索外,電影在氣氛營造上始終保持著一種緊繃感。攝影機有如雷扎的雙眼通常,警覺地觀察著周遭,觀眾們或許也站在了這一視角上,不禁心也跟著揪緊,懼怕雷扎一不當心說錯一個單字,小命就此不保。
做為俄羅斯、格魯吉亞和奧地利的合拍片,《波斯语课》代表格魯吉亞角逐去年的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導演獎,儘管未予提名,但贏得送選資格也證明電影的質素上佳。更重要的是,這種的合拍模式看似稀鬆平時,但曾經兵戎相見的國度,能聯手以表演藝術的方式銘記這段慘痛的發展史,這是來之不易又值得珍視的共識。
沒有明星,絕非出自於名導之手,也沒拿過大獎,《波斯语课》這種一部連名字都冷到沒用的電影,依靠不脛而走的好口碑,在今年的上海影展上,一票難求。出乎意料的是,這么一部絕非荷里活出品的影片在3月19日正式步入院線放映了。對視效商業大片不甚哮喘、偏愛文藝片的觀眾們而言,無疑不容錯過。
除了科赫與雷扎的朝夕相處外,電影也在男男女女的納粹黨戰俘及軍人頭上著墨很多。儘管對於自己的刻劃並沒有太深入,但不難看出自己頭上普遍具備的莎拉·阿倫特所謂的“平庸之惡”。一方面,自己有如普通人一樣,忍受著思鄉之苦,渴望著真愛的滋養;另一方面,被納粹黨的管理體制與價值觀所裹挾的自己面對猶太人,能毫不猶豫地開火,沒有半點憐憫之心。
但是,造詞容易,要一字不差地記住他們瞎掰的單字可就難了,在與科赫打交道的過程中,雷扎盡全力又如履薄冰,歷經死裡逃生,總算獲得了科赫的信任,並等來了能真正運用“阿拉伯語”的機會。
起初,對於科赫而言,雷扎的促進作用就在於傳授給他阿拉伯語,以保證他在戰後能去巴格達開餐廳,與惟一的哥哥團聚;而對於雷扎而言,科赫就像是一隻惡魔,他要想盡辦法安撫他,保證他們能虎口脫險。兩人的關係貼切而冰冷,沒有《钢琴家》裡那種正直感情在,這也是為什麼當科赫察覺到雷扎可能將在矇騙他時,馬上怒不可遏地把他打個半死。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報道,更多原創資訊請瀏覽“澎湃新聞報道”APP)
就連之後對雷扎表現出善意的科赫也不例外,他特別強調他們絕非劊子手,潛臺詞是“我只是個洗衣服的”,有如海因裡希·艾希曼在審判席上宣稱“他們是曲軸控制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裝置的促進作用而已”。
之後,科赫通過雷扎,順利完成了自我救贖,可能將是他在前者頭上看見了哥哥的影子,也可能將是兩人長時間的攀談令他感受到了交貨真誠的親情。但是,雷扎卻沒有被科赫對他的善意打動,在他眼裡,科赫和戰俘營裡的其它波蘭人並無二至;真正觸動雷扎的還是同胞,親眼目睹自己的慘死,令他實現自我身分尊重的覺醒。
《波斯语课》海報
劇中有多處通過較為的表現手法,展現出平庸之惡的麻木性。其中更讓人第一印象很深刻的是幾段裸體的呈現出:其一,是年長的奧地利戰俘偷看心儀的男子泡澡,臉紅心跳又提心吊膽;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攝影機俯拍置放在手推車上的層層疊疊的猶太人遺體。
堅信許多看了《波斯语课》的故事情節梗概,乃至看完影片本身的人,都會聯想到羅曼·立陶宛斯基主演的《钢琴家》。但這只不過是三部很不一樣的電影。在《钢琴家》中,主角與納粹黨軍人的關係是基於表演藝術共鳴上的心靈知己。而在《波斯语课》中,雷扎和科赫兩人關係的其本質還是把對方當做工具。
《波斯语课》翻拍自已六十高壽的奧地利知名編劇漢斯·塞爾哈澤(Wolfgang Kohlhaase)所著的長篇小說,故事情節本身受到真實該事件啟發,由白俄羅斯出生的導演瓦迪姆·米爾曼(Vadim Perelman)搬上大熒幕。
《波斯语课》劇組照,編劇瓦迪姆·米爾曼(左)與執導納麥克·佩雷茲·畢斯卡亞特
電影所呈現出的這段世間奇事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法國的第一所戰俘營內,一個宣稱他們是拜占庭血統絕非猶太人的比利時青年倖免於難,其原因在於負責管理戰俘營飲食的奧地利軍人科赫一心想自學拜占庭語。實際上,自稱為雷扎的青年只不過一句拜占庭語也不能說,為的是活下去,他絞盡腦汁,決定自行締造一種嶄新的“詞彙”來冒充拜占庭語。
戈達爾在3D電影《再见语言》裡,以所指與能指的間離性,證明詞彙是虛妄的。而《波斯语课》則反其道而行之。在納粹黨眼裡,猶太人毫無存有價值,可以被輕易殲滅,有如詞彙裡的能指可以隨意發生改變。但通過雷扎自創的單字,自己在戰俘營裡重新贏得價值。就似的影片開頭,納粹黨將猶太人的名冊焚燬,企圖徹底抹去自己的存有,但即使自己回到了雷扎的記憶中,因而有了超越姓名本身的象徵意義,也證明了詞彙是比槍彈更有力量的槍械。
有意思的是,就自我意識的失去上看,科赫和雷扎倒是公平的。最初,雷扎受求生的終極本能驅使,同樣無暇去思索,可以毫不猶豫地否定他們猶太人的身分。對於同類的憐憫之心也罷,對於族群的尊重也罷,原先都是人之為人的立身之本,但在管理體制與求生欲面前,都能被暫時擱置。
このサイトは、映画のポスター、予告編、映画のレビュー、ニュース、レビュー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映画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す。私たちは最新かつ最高の映画とオンライン映画レビュー、ビジネス協力または提案を提供します、私達に電子メ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著作権©2017-2020 920MI)。メー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