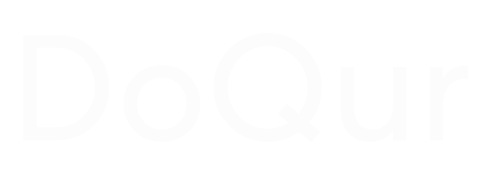雲中之國,一顆編劇白矮星升起!
《嘿玛 嘿玛》和《鲁纳纳之歌》就像是“尼泊爾的夜與日”。
就像趙婷在《骑士》中做的那般。她首先發現了一名在賽事中傷勢的牛仔布拉迪,追隨他重回綠茵場的過程並將那段觀察和經歷攝製成了影片。等同於是圍繞著真實的人物和生活環境去撰寫影片故事情節。
《嘿玛 嘿玛》
和國人熟識的電視節目《变形记》所反覆深入探討的一樣,環境和生活的發生改變其本質上是一場價值觀念的革命。
在只有9名中學生的魯納納中學,烏金不但看見他們,看見夢想的遙不可及,還看見魯納納人對基礎教育和夢想的珍惜。
難能可貴的是,電影並沒有盲目堆砌符號化的民族樂器元素,而是通過相同的音樂創作場景,循序漸進地把音樂創作彌合三個世界的過程徐徐展開,很有立體感。
一路取用著犛牛糞的烏金,在小學生用盡了他們帶來的油墨之後,摘下了他們臥室裡用以封住玻璃窗保暖的尼泊爾紙,裁剪成筆記本電腦發給小學生,一方面順利完成了他對當地環境的徹底融入,另一方面實現了他以看淡生存市場需求置換思想市場需求的蛻變。
故事情節最後,烏金如願以償走進澳大利亞。喧鬧的夜總會里,烏金獨自一人自彈自唱著英文歌曲,他就像水蒸氣,融入了夜總會大背景音中。他一定在想:這為什麼就是所謂的音樂創作夢想嗎?
實際上,假如我們留意觀察,烏金被《圆满牦牛之歌》“喚起”了三次。一次在電影開場,一個神祕背影面向雪山唱著歌。攝影機一切,好似嗓音喚起了在賴床的烏金。當時喚起的是烏金的皮膚,片頭此次,嗓音幫助他喚起了他們的靈魂。
這首歌曲對烏金的吸引是多方位的:達爾頓的感人唱功、獨有的唱腔,歌詞中的神話傳說。他著迷這首歌曲,為的是學會唱,將歌詞抄錄在澳大利亞移民計劃宣傳單上,隨身攜帶。這張宣傳單曾經是烏金返回都市文明的希望火種,被他視如珍寶,現在寫滿了《圆满牦牛之歌》。
“世界公民”一代的身分大背景,讓他們在面對獨有的土著人文時掌握了一種更為宏觀經濟的視野和先天的分寸感。他們既不敢向一方水土索要什么,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應將任何信念強加在原始的農地和人文上。面對當地社會與人情的轉變,不用承載原生報復,經典作品表達常常因冷靜而敏銳。
電影開篇烏金和教育部長討價還價的戲,對白寫得尤其有意思。在兩人的見招拆招中,潛移默化地交待了那個將“美好指數”視作頭等大事的國家的種種現實生活對立,還處處透著冷幽默,為影片訂下了一種類“脫力系”戲劇的調子。
掃碼即享VIP會員9.9元包月特價購
比如說烏金一聽他們要被派去魯納納,就連打退堂鼓,疾呼他們有“高山症”。教育部長哪是等閒之輩,直接懟回來一句“高山症?你還是尼泊爾人嗎?”揶揄烏金並非“高山症”而是“大頭症”。
《鲁纳纳之歌》的故事情節就從烏金的最後兩年學生合約講起。原來身為年輕一代的烏金對尼泊爾之外的曠闊世界期待已久,已經對廷布一成不變的生活深感厭倦。他說英語、唱英語歌、泡酒吧,喝洋酒,計劃移民澳大利亞去追求他們的音樂創作夢想。
在魯納納的最後時光,達爾頓牽來犛牛,讓烏金養在教室裡。她說魯納納人世代牧牛,之所以把名為諾布(意為珍寶)的犛牛贈送給烏金,即使對魯納納人而言,烏金是能“摸到未來的人”,就是自己的珍寶,烏金上輩子也許是一隻犛牛。
《鲁纳纳》中的對白,多半都有著多樣的潛臺詞涵義,很耐吞嚥。
僅在亞洲地區方面,近幾年就有女王逸的《别告诉她》和李·以薩克·鄭主演的奧斯卡金像獎大熱門《米那里》引起探討。在那些經典作品中,家庭感情是故事情節的依託,人文尋根與身分尊重主題被置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
3年後,帕武·多傑面世了他們的編劇成名作——故事情節長片《鲁纳纳之歌》(又稱:《教室里的一头牦牛》)。
前者透過大量的宗教信仰記號與典禮,探祕尼泊爾王國古老神祕的另一面,後者則通過一個成長故事情節,在熒幕上展現出一個現代文明滌盪中的更為真實的尼泊爾。
堅信看完《鲁纳纳之歌》,你會開始關注帕武·多傑那個名字。
抵達魯納納之後的最後一座休息站名叫科那,平均海拔3100米,只住著一戶人家:普巴與央真妻子和自己的幼孩。區區3人,也把自己清清楚楚標示在熒幕上。
由此,教室裡的一隻犛牛,既指諾布,也是烏金。
後來全鎮老少集體出動,用一場大合唱迎接烏金。這首純樸原始的演出,讓浸淫在流行樂詞彙中的烏金大受震撼,他見識到一種他們還無法理解的音樂創作力量。
在這種一個參照座標系中去觀察帕武·多傑的《鲁纳纳之歌》,總覺得他與出身上海,唸書於英美,在創作中深入關注英國中西部的趙婷或許更加接近。
一句“瘦了”,去除長輩對晚輩的關照,還有“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反差式喜劇效果。順便表示了從前在尼泊爾“女人要虎背熊腰就可以找出老公”,現在卻都追求身形消瘦的審美觀變化。
第二堂課,一個男孩站起來,說他們長大後想當一位學生,即使學生是能“摸到未來的人”。小班長佩珠站起來,說他們想成為一位女歌手,被要求上臺跳舞時,竟毫不怯場地大唱情歌,讓之後在夜總會里很多唯唯諾諾的烏金頗受觸動。
冉冉升起的“無界作者”
《鲁纳纳之歌》的編劇帕武·多傑,就是很值得看好的一名。
《鲁纳纳》並不故意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脫落和矛盾大書特書,更沒有堆砌少數民族人文記號。它完全依靠絕妙的對話,樸實生動的人物細節,用寥寥兩場戲就創建起多層次的尼泊爾生活圖景。
教育部長那個人物雖然上場短暫,卻全然並非刻板的官僚讀法,道出了一種在尼泊爾那個人口數70多萬的小國家中,既威嚴又親切的那種立法權關係。
困窘與困苦中,烏金停了下來,隨即音樂創作風格一轉,唱出了一曲《圆满牦牛之歌》,整個夜總會為之沉靜下來。這無異是電影聲音上的夢幻時刻——烏金再也不是傳遞異國音樂創作的這種用具,他成為了他們內心世界的音樂創作源頭。
烏金的爺爺,是另一個上場自帶信息量的配角。她另一面在家裡虔誠誦經,儼然一名和藹可親長者,但卻犀利吐槽侄子烏金是個“廢柴”,譏諷烏金身形魁梧的好友“瘦了”,實則一名龐克毒舌老伯。
從古老與神祕中走出來的帕武·多傑用獨立主演的《鲁纳纳之歌》證明他的創造力。他已經是一名既能夠用高度風格化的影片詞彙駕馭傳統人文題材,又能給文學故事情節注入新鮮靈氣的青年影片作者。
烏金和魯納納最重要的共同語言是音樂創作。愛好音樂創作的烏金在人生茫然時走進高原上的“音樂創作之巔”魯納納,好似便是這種古老法力降下的神祗。
帕武·多傑創作《鲁纳纳》也是同樣的思路。他先結識了尼泊爾音樂創作人希拉布扎西(Sherab Dorji),依照希拉布扎西計劃移民澳大利亞,追逐音樂創作夢想的真實經歷締造了烏金那個人物並邀請希拉布扎西在影片中出演烏金。
這種的作法,與其說是打破了真實與虛構的界線、專業與非專業演出的界線,倒不如說是從終點開始就完全不受所謂界線的綁縛,既不截取、也不安插,讓故事情節和人物從原始的沉積物中自然生長出來。
於是乎,青年教師烏金告別首都廷布,向世界盡頭的魯納納中學駛去。
《旺扎的雨靴》
接著是小佩珠的嗓音。佩珠和烏金一樣,是個雙親缺位,隨爺爺長大,以女歌手夢想維生活動力的小孩,是烏金內心深處的這種二維。
我們還將為大家送出《鲁纳纳之歌》免費暢看兌換券
二人的經典作品中,皆有大量對人文景觀的呈現出。電影中魯納納的部份,人物經常退居天際線下一個小點,更有很多對話場景,在大遠景攝影機中實現。相較於表現家庭,自己更為關注曠野中的個體,擅於洞悉環境促進作用在人物內心世界的傷痕。
起初烏金對高原生活充滿著牴觸。他用播出著流行樂的音箱,國際品牌防風服和信息技術布料山地鞋政府軍他們,對傳統飲食中的檳榔、夜裡篝火旁的古老歌謠,最低山口上的供養祈福傳統上演了“婉拒三連”。
在內容層面,《鲁纳纳》或許與華語觀眾們較為熟識的“藏地新浪潮”一脈經典作品有著近似的關注點。
尼泊爾高原上演“變形記”
烏金意識到,音樂創作在近乎與世隔絕的魯納納有著多么關鍵的象徵意義。以致於他後來大費周章從衛星城運到他們的電吉他,教孩子們一邊跳舞一邊自學。與之後對當地的婉拒立場迥異,烏金自此時開始將他們生活的關鍵部份搬遷到魯納納,紮下音樂創作的根。
電影適時地採用片頭標示出了此種數字上的變化,與尼泊爾當地的高海拔地形客觀匹配。
讓他開始融入當地的,首先是極端惡劣的生態環境。比如說最終為的是禦寒而勉強食下的檳榔,隨身聽電量耗盡之後而被迫摘下的音箱,進而讓烏金的雙耳第二次灌入山林的聲音,再比如說這個破舊不堪的,錯掛了英語“浴室(Kitchen)”標識的室外洗手間。
2016年,《嘿玛 嘿玛》(Hema Hema: Sing Me a Song While I Wait)闖進華語粉絲的視野,可說是一筆熒幕異色。
而讓烏金真正採納這一切乃至願意留下任教的,是平均海拔4800米上生活著的56個魯納納人。
《鲁纳纳之歌》正在歡喜首映禮APP全網獨播
影片早前已在數個國際影展現身,收穫了不錯的口碑,現如今更代表尼泊爾參予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導演獎的競逐。該片已上線歡喜首映禮獨家播映。
那個小細節不但在劇中營造了具備說服力的空間感,進一步增強前半程旅程部份的紀實效果,同時一步步推著觀眾們和烏金一同,越往上爬越丟下宗教的評價體系,採納高原上的地廣人稀和與之帶來的生存價值觀念。
帕武·多傑自身與尼泊爾的血脈聯結和他“世界遊民”的身分,賦予《鲁纳纳之歌》一種並不多見的微妙距離感。
真的鬥不過教育部長的烏金,為的是保全他們的澳大利亞音樂創作夢,只得硬著頭皮應下那個任務。在他的盤算中,如果熬過短短的兩年,待夏天大霧封山之後,就能順利完成合同恢復自由身,奔向澳大利亞新生活了。
廷布的繁華程度尚且無法滿足烏金,更何況是高原上貧窮落後,缺水缺電的魯納納。
在帕武·多傑的成長過程中,他的足跡遍及尼泊爾、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比利時和英國多地,常年以攝影師身分活耀在尼泊爾與巴基斯坦。
在追逐音樂創作夢想中所經歷的傳統與盛行的武裝衝突問題,讓人聯想起德格才讓的《他与罗耶戴尔》。當地人家無比珍惜的塑料靴或許與拉華加《旺扎的雨靴》形成呼應。以古老神話為標的,引領觀眾們去思考少數民族與身分問題,是萬瑪才旦經典作品中常用的主色。
在尼泊爾,一份“為中央政府處事”或“為一世處事”的工作,是當地人眼裡再好不過的差事。生活在首都廷布的烏金扎西就是這種的“幸運兒”。他與尼泊爾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簽訂了三年學生合約,或許是那個號稱“世界上美好指數最低”的國家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人了。
《米纳里》
在這兒,駱駝是無比關鍵的夥伴,介紹名字的這時候甚至要排在人的後面;在這兒,衣服是稀有資源,只有家中最被倚重的小孩能穿;在這兒,家家戶戶多半隻有一頭竹製或是木製的碗,要留給最尊榮的遠方顧客就餐。
在創作表現手法上,傾向於通過觀察真實人物和該事件去生髮影片文檔。
烏金的計劃很快受挫。在造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的這兩天,他遭受晴天霹靂,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長安排到全尼泊爾最偏遠最低平均海拔的魯納納中學去任教,堪比被髮配到被世界遺忘的角落。
和同學一樣受到重視的,是魯納納心靈之源——犛牛。犛牛糞能燒爐子取暖,剩下的炭渣能漆成黑板,同時供給生理市場需求和思想市場需求。
放眼海外,面對一片若即若離的“故土”,做為“去者”和“歸來者”,怎樣理解當地人文傳統和社會習俗在歲月中的變遷,或許是初出茅廬的極少數族裔電影人樂意去表現的主題。
影片的班底足夠多精采:由宗薩欽哲仁波切編劇,田壯壯任剪接,周迅和郭富城驚喜客串演出,而擔任製片人和執行編劇的是青年電影人帕武·多傑,他還有一個較為人津津樂道的身分是劇作家賴聲川的外甥。
首都廷布至魯納納之間的長途旅行依照垂直方向緩緩展開,越接近目的地平均海拔越高,人口數越稀少。
大量的音樂創作場景讓《鲁纳纳》一直維持極高的“可聽度”。其中最更讓人第一印象深刻的一首曲目是牧羊女達爾頓唱出的《圆满牦牛之歌》。
旅程中,當夜幕降臨,魯納納人米臣自然而然地和夥伴唱出歌謠。就算烏金還死命扣著音箱,也無法遏制他們被悠揚的嗓音吸引。那個這時候的他還只是小有動心。
長期以來,“跨界”電影作者備受矚目。但是隨著多元群體經濟發展漸漸成為主流,地緣關係與文化邊界異常活耀,即使是在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這種的先天“排他”的大獎類別中,也能看見愈來愈多的無法按照既定界線去框取的經典作品,而那些經典作品背後將湧現出數百名難以通過詞彙、地域、或者類型界定的電影人。與“跨界”相對應,自己就像是一大批“無界作者”。
タグ 魯納納之歌 魯納納 騎士 他與羅耶戴爾 教室裡的一頭犛牛 旺扎的雨靴 變形記 嘿瑪 嘿瑪 圓滿犛牛之歌 別告訴她 米納裡 米那裡
このサイトは、映画のポスター、予告編、映画のレビュー、ニュース、レビューに関する総合的な映画のウェブサイトです。私たちは最新かつ最高の映画とオンライン映画レビュー、ビジネス協力または提案を提供します、私達に電子メ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著作権©2017-2020 920MI)。メール